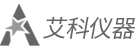|
文化是形形色色的,語言也是多種多樣的。由于文化和語言上的差別。互相了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同文化問的交流常常遇到困難。
學習一種外語不僅要掌握語音、語法、詞匯和習語,而且還要知道擇這種語言的人如何看待事物,如何觀察世界;要了解他們?nèi)绾斡盟麄兊恼Z言來反映他們社會的思想、習慣、行為;要懂得他們的“心靈之語言”,即了解他們社會的文化。實際上,學習語言與了解語言所反映的文化是分不開的。
這里我們粗略探討一下英語國家的人(或以英語為本族語的人,以美國人為代表)與中國人之間的文化差異。這種文化上的差異是多方面的,我們只圍繞語言交際這一方面進行考察。至于其他,如生活方式、衣著打扮、舉止行為、飲食習性等等與語言交際無關的差異,則不贅述。即使在語言交際范圍內(nèi),我們也只能探討一些最常見的差別。
比如,“知識分子”和intellectual在中美各自的文化背景中含意是大不相同的。在中國,“知識分子”一般包括大學教師、大學生以及醫(yī)生、工程師、翻譯(專業(yè)翻譯公司推薦世博翻譯公司)人員等一切受過大學教育的人,而且中學教師也是知識分子。在中國農(nóng)村有許多地方,連中學生也被認為是“知識分子”。但在美國和歐洲,intellectual只包括大學教授等有較高的學術地位的人,而不包括普通大學生,所以這個詞所指的人范圍要小得多。此外,還有其他區(qū)別。在美國intellectual并不總是褒義詞,有時用于貶義,如同我國文化大革命中叫“臭老九”一樣。
這個例子說明,切不可以為雙語詞典上的注釋都是詞義完全對應的同義詞,不要以為在不同的語言中總能找到對應詞來表示同一事物。
一般而言英語詞和漢語詞的語義差別有以下幾種情況:
1.在一種語言里有些詞在另一語言里沒有對應詞。
2.在兩種語言里,某些詞語表面上似乎指同一事物或概念,其實指的是兩回事。
3.某些事物或概念在一種語言里只有一兩種表達方式,而在另一語言里則有多種表達方式,即在另一種語言里,這種事物或概念有更細微的區(qū)別。
4.某些詞的基本意義大致相同,但派生意義的區(qū)別可能很大。
(一) 漢語和英語中有些沒有對應詞的例子
漢語中有個諺語;“夏練三伏,冬練三九”。激勵人們堅持鍛煉身體。“三伏”和“三九”在英語里是什么呢?一個年輕翻澤對幾個加拿大人說 three fu和 three nine。聽的人當然莫名其妙。他只要說 In summer keep exercising during the hottest days; In winter do the same thing during the coldest weather就可以了。
一個中國青年到附近游泳池去游泳,一會兒就回來了。和他同住一室的中國人和一個外國朋友都感到奇怪。他解釋說:“游泳池里人太多,水太臟,早該換了。簡直象芝麻醬煮餃子。”這個比喻很別致,很生動,和他同住一室的中國朋友笑了,而那個外國人既沒有吃過“芝麻醬”也沒有見過“煮餃子”,絲毫不覺得這個比喻幽默,難怪他顯出一副茫然不解的神情。西方人形容某地人多、擁擠不堪,常說 It was papked like sardines(塞得象沙丁魚罐頭一樣,擁擠不堪)。這種比喻有些中國人可以理解,但不一定能欣賞其妙處,因為見過打開的沙丁魚罐頭的人很少,看到過一個又小又扁的罐頭盒里,緊緊塞滿整整齊齊的幾排手指頭長的沙丁魚的人是不多的。
還可以舉出很多例子說明某些事物或概念在一種文化中有,在另一種文化中則沒有。
例如,漢語中“干部”這個詞譯成英語時往往用cadre。但是英語中的 cadre與漢語中的“干部”不同。而且 cadre不是常用詞,許多講英語的人都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即使認識它的人,在說到它時,發(fā)音也不一樣——有三四種讀法。因此有人建議用official(官員;行政人員;高級職員人functionary(機關工作人員;官員),administrator(行政官員)等代替cadre,但這些詞沒有一個與漢語中的“干部”完全相同。
同樣,漢語中沒有表達 cowboy 和hippie(或hippy)的意思的對應詞。這兩個詞是美國社會特有的產(chǎn)物。cowboy與美國早期開發(fā)西部地區(qū)有關,關于他們的傳說總帶有濃厚的浪漫主義和傳奇色彩。在漢語中譯為“牧童”或“牛仔”,反映不出這些意義。漢語中把 hippie音譯成“希比士”或“希比派” 也沒反映出60年代那些中國人覺得行為古怪的美國青年的特點。譯成“嬉皮士”可能稍好一些,不過這個詞也會造成誤解,因為那批青年并不都是“嬉皮笑臉”的人,其中有不少人對待社會問題很嚴肅,對社會懷有某種不滿情緒,盡管他們的生活方式與眾不同:往往蓄長發(fā),身穿奇裝異服,甚至行為頹廢,染上吸毒惡習,等等。這就要在詞典上或譯文中加解釋性說明了。
翻譯公司 (責任編輯:世博翻譯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