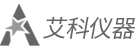|
3(世博北京翻譯公司))詞句的重復與修辭格的廣泛運用
詩歌中常重復一些詞句或詩行,用以抒發(fā)真摯深沉的情感,或是用以渲染某種氣氛(如回環(huán)往復的纏綿),或是用以增強詩的歌唱性。詩歌中又大量運用修辭格,尤是是各種各樣的明喻、暗喻、比擬用得最多。
4) 豐富的意象與象征
所謂意象,是指那些可以引起人的感官反應的具體形象和畫面,分為視覺、聽覺、嗅覺、觸覺、味覺、動覺、通聯(lián)等。這些意象不僅喚起人們的某種體驗,更常常具有鮮明或隱晦的象征意義,是許多優(yōu)秀詩篇所具有的共性。
(二) 詩歌的翻譯
如果說翻譯難的話,那么最難莫過于譯詩了,尤其是格律詩,所以古今中外常有"詩不可譯"的聲音。其實,說"詩不可譯",主要是指詩味難譯,詩的音韻美難譯,并不是說詩歌不能翻譯。再者,詩有不同的詩:有的明白暢曉,有的艱深晦澀,有的韻律嚴整,有的不受律法所限。譯詩者也有水平高低之分、技藝優(yōu)劣之別,所以更客觀地講,詩難譯但并非不可譯。
一般說來,語言形式服務于內(nèi)容,并具有一定的意義。就詩歌而言,形式的意義遠遠大于散文類作品中的語言形式。詩之所以成為詩,怎樣說與說了什么同樣重要,所以譯文中追求形似是譯者的重要任務之一。在我國的譯詩史上,有將英語格律詩譯成元曲形式的,有將它譯成五言古體形式的,還有用騷體譯出的。但目前看來,采用這些形式都值得商榷,因為英語詩人絕不會寫出唐詩宋詞。同樣的原因,把英語格律詩譯成散文或散文詩(如梁遇春譯雪萊的A Lament)也是不可取的,因為詩歌的形式是有意義的。
英文格律詩漢譯的另一種方法是"以頓代步",即以漢語的"頓"代替英語的"音步"以再現(xiàn)原詩的節(jié)奏。"以頓代步法"通常強調(diào)原文的韻式也應在譯文中加以復制,即如果原文的韻式是ABAB、CDCD,那么譯文也應有同樣的韻式。所謂"頓",是指兩個、三個抑或是四個漢字放在一起,它們構(gòu)成一個相對完整的意義,同時又形成語音的一種自然的起落。這確實有點像由輕重抑揚構(gòu)成的音步。以這種方法譯詩,是譯者追求形似并再現(xiàn)音美的大膽探索,而且確實也產(chǎn)生了一些形神皆似的譯作。不過,在頓與音步的對等方面以及頓在何處(即在何處停頓)等問題上,翻譯界仍有爭議,譯者自己有時也難以把握。
英語格律詩的另一種譯法就是放棄韻律,用自由體翻譯,持此論者的理由是原詩節(jié)律在漢語中無對等物,譯詩重在傳達神韻,形似難求且束縛表達,因此不如棄之。在追求形似上,我們認為,王佐良先生提倡的"以詩譯詩"是完全正確的,詩歌畢竟不是散文,因此,原詩如果有韻,那么譯詩也應盡量沿用;原詩如果無韻,譯詩也應無韻,即使用韻,也不能太過整齊,只應是個別詩句中用韻。原詩的節(jié)奏應盡量用漢語的自然起落體現(xiàn),但不可偏執(zhí),非要找到所謂"頓"與"音步"的等量齊觀不可。形似應盡量在用韻與否以及詩行長短上予以體現(xiàn),這樣既保存了原詩的形,又再現(xiàn)了原詩的音美。
當然,詩之最大功用是言志言情。傳達情志當為譯者首先必須考慮的事情。對于大多數(shù)詩來說,形式雖也有意義,但相對于詩之神韻和意境而言,它仍處于次要地位。英漢語言及文化的差異常要求譯者"變換說法",即變換形式以求神似。比如我們雖不贊成將英語格律詩全都譯為中國五言或七言詩,但以這種形式譯出的某些詩如能做到傳神,卻也不失為好的譯作。詩歌形式中確有一些不可譯因素,但詩的意義、意境、神韻卻大都可以被意會、被言傳,盡管難以全部傳達。因此譯者應在詞語的錘煉上下苦功夫,寫詩者常常是"語不驚人誓不休",譯詩者沒有這種精神也休想"譯語驚人"。
試比較下面一個英語詩節(jié)的漢譯:
The curfew tolls the knell of parting day,
The lowing herd wind slowly o'er the lea,
The plowman homeward plods his weary way,
And leaves the world to darkness and to me.
譯文一:暮鐘鳴,晝已暝
牛羊相呼,迂回草徑
農(nóng)人荷鋤歸,蹣跚而行
把全盤世界剩給我與黃昏 (郭沫若譯)
譯文二: 晚鐘響起來一陣陣給白晝報喪,
牛群在草原上迂回,吼聲起落。
翻譯公司 (責任編輯:世博翻譯公司) |